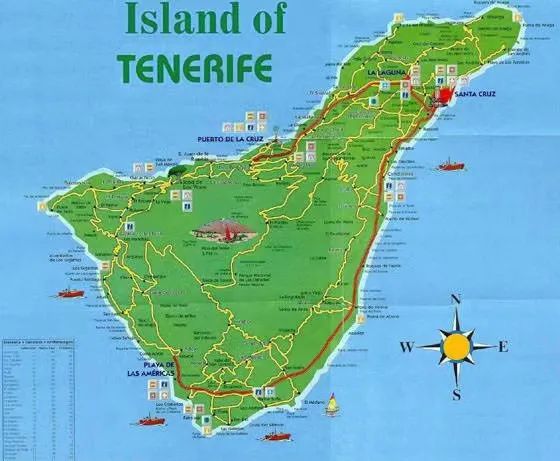张军当代黄鹤楼·江山遗迹(纸本水墨)

□ 白愈伤组织
城市被视为人类成熟和文明的重要标志。从近代以来的理性主义角度来看,城市被视为人类聚居的最高形式,因而具有巨大的人口吸引力。除了近代中国可以在短时间内建成一座城市外,大多数知名城市都有着悠久的历史。而其背后,则是人与自然、文化、权力、贸易,甚至个人想象和集体记忆之间复杂的博弈。李路平的《武汉传》对于地理意义上的城市如何转化为概念性城市形象提供了极其严谨的解读和建构方法。

在他的传记中将武汉列为“丝路百城”之一,在规划者的期待和作者的设想中,武汉不只是被视为矗立在华中大地上的一个具体地方,而是一座中国城市。武汉是一座现代化的国际大都市,它的想象超越了有限的地理界限。与外界的关系是作者讲述武汉最重要的出发点。无论是盘龙城出土的文物与中原江南地区的文化联系,还是“武汉”这个名字出现之前曾经穿梭、驻守行政的历史人物,还是古代的盐、铁、汉诺国际港对中国和世界的贡献,彰显了武汉在文化、政治、军事、商业等方面的卓越地位。尤其是人物。从糜衡、元稹到曾国藩、张之洞,无数名噪武昌、汉口等地的历史人物,都是与中华文化历史休戚与共的人物。如果换个角度看,作者的理念隐含着“不谈武汉就无法讲述中国和世界”。在笔者看来,武汉不仅是江汉平原“固有”的,而且构成和指涉着世界。
尽管本书的范围超越了地域界限,但作者的叙述源头却来自于武汉的“根”,即长江和汉江。 “江汉交汇的大都市”不仅作为该书的副标题,也是武汉的地理坐标。在开篇有关《武汉在哪里》的陈述中,书中给出的标志性指引就是江汉交汇点。长江为“经”,汉江为“纬”。 “四到”也可以看作进出武汉的两条大河。具体位置。在这片水网密集的广阔区域,山、湖、岛、岛自然交织,却也是武汉人历代以来赖以生存的家园。两条河流成为作者想象和描述武汉的主要依据和线索,清晰地捕捉到了江城区别于其他城市的独特之处。作为对武汉的“百科全书式”解读,本书蕴藏着丰富的科学自然、地理、人文知识,不仅让世人对武汉的认识和想象变得清晰具体,也支撑了作者用文字来完成对武汉的理解和想象。以叙述的方式讲故事。武汉城市形象的全息构建。
如果没有人的进入和命名,自然就没有任何意义。江汉成为武汉的过程,也是客观世界向意义世界转移的过程。武汉城市形成的历史,实际上就是自然空间改造的历史。这种转变不仅是先民通过生活实践将自然构建为城市空间,也意味着对武汉的想象将现实中的武汉转变为我们必须了解武汉的概念,否则它无法成为一座城市。人文意识。这本书的名字叫《武汉传》。 《传记》是一种历史叙事,也是对武汉作为一个空间的文化身份的确认。作者在创作中塑造了武汉,并采取了将空间“历史化”的方法,形成了“历史空间化”的同一枚硬币的两面。这种叙事方式使本书区别于许多客观的关于武汉的介绍性著作,成为作者自我情感和主观认知的审美表达——不仅是对文本,也是对这座城市本身。悠远而庄严的历史背景、烟火升腾的丽芬生活、“光谷”所蕴含的发展潜力,更多的是一种叙事姿态,而不是对武汉城市形象的描述。
就像一条河流在大地上蔓延、渗透,作者沿着空间地理的叙述引出与之相关的历史和人物,为叙述勾勒出清晰的脉络。以长江为界,南北古城是连接武汉前世今生的媒介。从金口到“沙县”,从荀子的记载到秦始皇分天下,到黄祖迁都却越城,江水流去却尘埃满是历史的沉积;汉水改道,将汉口和汉阳分开,一条淮盐巷见证了范仲淹、张伦接手筑堤保护盐田;从汉江南岸曾经矗立的烟囱中,浮现的是张之洞实业救国的雄心……文字中奇异的时空交汇,揭示的是武汉的人文之谜。历史在这片土地上不断积淀、积淀的精神。由点到线,再由线到面的叙述,最终结合了武汉作为文化空间的形象,也从历史深处呈现了武汉蜿蜒的轨迹。其中,作品不仅勾勒历史上的武汉与“丝绸之路”的关系,还着力描绘现实中的武汉,特别是进入新时代后的武汉。

更难能可贵的是,在为读者构建一个既有历史深度又有现实视角,又有精神内涵和文化温情的城市形象的过程中,作者通过史料梳理、实地走访,呈现出强烈的真实性。 -寻求态度和认同。力量。每一座有历史的城市,都有一些不清楚甚至被误解的细节,武汉也不例外。然而,在本书中,作者像显微镜一样观察所有材料,并试图尽可能清晰地识别出含糊之处,以免误导后人。这是作者作为一个“老武汉”的文化责任。例如,咸丰之战后重建黄鹤楼,后世志记载“由总督管文、李含章、总督郭伯殷主持”。然而,笔者研究得出的结论是,两位总督并不具备建造黄鹤楼的条件,而且编年史不仅混淆了李鸿章兄弟的名字,而且给了他们错误的功劳;又如,历史上题写“艾远”称号的人是“吴百花学士”,但笔者查考经典,却没有找到踪迹,实际上是“学使吴百花”的错误。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正是作者的精心研究,才还原了历史的本来面目。
台湾学者陈熙源写了一篇题为《人走楼倒水自流——论位于文化史上的黄鹤楼》的文章,观察文字传统中的黄鹤楼对后世的影响。 。 1884年9月22日(光绪十四年八月初四),一场大火烧毁了黄鹤楼(郭伯因等人所建)。后来,张之洞在旧址上修建了一座二层小洋楼(警钟楼)。 ); 1955年修建长江大桥时拆除了这座小洋房,1985年在原址上重建了钢筋混凝土黄鹤楼。从1885年到1985年,可以说没有黄鹤楼世界上,陈熙媛却发现,它依然站在文人眼中。在没有塔的百年里,康有为写了《登黄鹤楼》,黄遵宪写了《登黄鹤楼》;刘师培在《黄鹤楼夜景》中更是用极其优美的文字描述了登塔时的所见;就连毛泽东1927年视察武汉时,也写下了《蛮夷菩萨登黄鹤楼》,无论文字和图像多么精妙,也无法将客观事物转移到纸上。只有通过描述和想象,易逝的现实才能永垂不朽。就像黄鹤楼形象的代际传递一样,在《武汉传》的引导下,我们不断丰富着对武汉的想象,按照我们的理想去完善她的形象——想象中的武汉显然比真实的更有能力。城市。它被充分地把握和感知,因此更有温暖。
(作者为中国作协网络文学委员会委员、河北省作协研究员)
版权声明:本文内容由互联网用户自发贡献,该文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本站仅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不拥有所有权,不承担相关法律责任。如发现本站有涉嫌抄袭侵权/违法违规的内容, 请联系本站,一经查实,本站将立刻删除。如若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s://www.fxk666.com/html/tiyuwenda/2068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