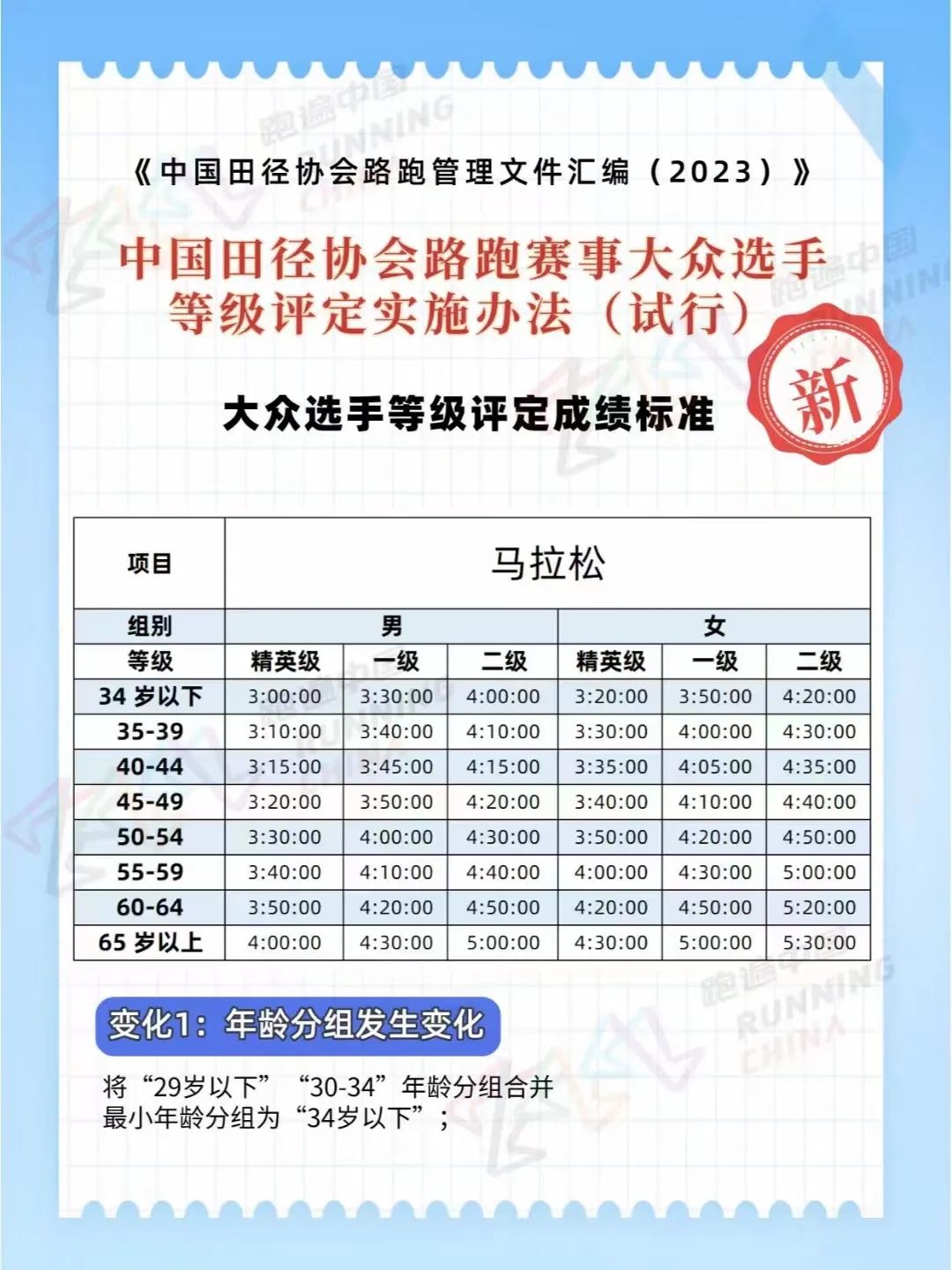自上世纪末以来,凯里市大十字路口聚集了一批技艺高超的苗族补补姑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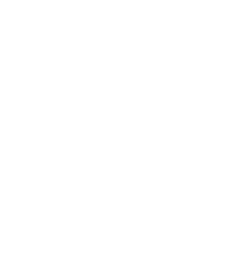
凯里最早的织补基地——大十字
一针、一根线、一个钩针、一件衣服、一个人、一颗心。
他们早上出发,晚上完成工作。几十年来,无数的衣服和棉线从他们的手下经过。岁月的痕迹悄然爬上额头。工作时那个眼神明亮、聪明伶俐的小女孩,现在变成了两鬓结霜、戴着老花镜的可恶女孩。
初秋的早晨,下着小雨,路人打着伞,行色匆匆。
中秋节临近,凯里市大十字嘉汇超市门口的花坛前整齐地搭起了一排白色塑料棚,作为商家的临时月饼销售点。可能是下雨的缘故,月饼摊还没有摆好。空荡荡的白色遮阳棚下,只有一个戴着粉色头巾的苗族妇女,坐在小马驹上,静静地缝补着,仿佛周围的一切都与她无关。

田映秀今年40岁,是织补女孩中年龄最小的。因为下雨,她是唯一一个准时从平时熙熙攘攘的补补摊出来的人,手里小心翼翼地缝着一件墨绿色的毛衣。 “我和客户约好了今天早上来取货,所以尽管下雨我还是来了。”正在修补的衣服上,已经布满了大大小小的十多个洞。田映秀像扫雷器一样,一一寻找着那些小洞。 ,然后根据破损处和衣服的缝制图案仔细修补。
要想做到“无痕”补缝,不仅线要按照衣服原来的纹路编织,而且补缝线也有讲究。她从衣服内部的接缝处取出它们。
早上8点,当她从摊位出来时,采访期间,她已经在细雨和寒风中缝纫了一个多小时。 “这件衣服的材质不错,但是价格贵,修起来比较费时间,要两个多小时,跟客户商定的价格是50元。”
补补一件衣服的价格从几元到几十元不等,基本定位为“大众价”。一般来说,顾客认为花一点钱换来修好的衣服是值得的。
过了一会儿,旁边的摊位上又来了一位补补的姑娘——50岁的潘阿友。她在这个路口缝纫了20多年,是最早来凯里补补的绣娘之一。
“当时凯里没有织补的人,我的一个亲戚会绣花,所以有人请她补衣服。当她发现织补能赚钱后,就把我带到了凯里,就在大十字这里。” ,为人们补衣服。”
后来,来补补的人越来越多,其中大部分是黄平、古龙、忻州等地有刺绣技艺的绣娘。高峰时,路口聚集了三十多个织补女孩。

2010年前后,生意最好。 “当时,虽然补补的人很多,但不用担心客流量,整天都没有闲着的时间,一天补七八件是常事。生意兴隆的时候,还好,白天能接到十多个订单,晚上就得带回家补了。”
随着国内生产力的不断提高,近年来衣服越来越便宜。只需几十块钱就可以买到新衣服。愿意花钱补衣服的人越来越少。织补市场也在萎缩。母亲的数量也在逐年减少。
几年前,凯里市为他们指定了两个便民点。 10余名绣娘搬到了韶山南路路口的摊位。大十字摊位上只剩下七八个人了,也不再像以前那样热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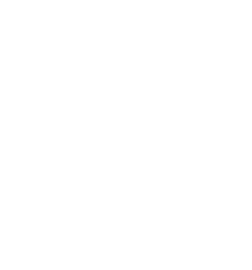
织补技艺的最佳老师——抹布
韶山南路便利摊正对着中银口岸。因为下雨,七八个补补的阿姨把摊位搬到了岸边的台阶上。
头戴黄平苗族特有的红色小圆帽,一人一马提着一个竹篮,竹篮里放着各种彩线,这是他们的标志性装束。

晴天晒太阳,雨天吃雨水,寒风刺膝,烈日灼伤皮肤。长年在街头打工,皮肤并不白皙,但这些爱美的苗族妇女大多都涂了粉底、涂了口红,不少人还戴着精致的银耳环,显得很漂亮。
坐在中间的几个人已经接到了活儿,正埋着头,手指在衣服上不断地起落,快得连手法都看不出来。
有的用苗语聊天,古龙的盘阿哥则伴着雨声悠闲地唱着苗歌,神情轻松又专注。旁边的姐姐听到她的歌声,自然轻声应道,但工作上却丝毫没有懈怠。
专注于触手可及的工作,默契在歌声中传达。他们都是来凯里谋生的黄平同胞。为了保证每个人都有活路,织补妈妈们商定了一套公平的规则:收到工作的人坐在中间,没有收到工作的人坐在两边。 ,这样无论客人来自哪里,首先可以询问的是没有领到生活饭的人,促进了姐妹之间的和谐。
来这里做补布生意的不仅是黄平人,还有不少是亲戚、师徒。织补行业的不成文规定是只有家庭成员才能接受培训。 48岁的潘文敏10多年前进入这个行业,受到姐姐婆婆的教导。虽然我从小就有刺绣功底,但织补之路还需要师傅走正路。
手工织补的工作原理是利用衣服原有的经纬纱,根据服装纹理进行二次织造,以达到与原有服装组织图案相结合的目的。一个优秀的补补女孩可以让破洞变得“完美”。织补完成后,将衣服平放,以便看不到修补的区域。听起来很简单,但实际上需要数千甚至数万次手工操作才能准确、熟练地完成。而且,并不是所有的布料都能精细补缝,这就需要补缝妈妈们动动脑筋,换线、改变色差等。
说到精细织补,最重要的是考验一双眼睛。要训练眼睛适应各种精细的图案和面料,最终达到“看不到布的图案,只看到组织结构”的状态。潘文敏跟着师傅,边学边做。刚开始的时候,三五天都拿不到订单,顾客大多还是信任老织补师傅。

经过日复一日的练习,潘文敏的织补技术越来越好了。一个月后,我基本上可以独立经营一个摊位,补补普通衣服也不再是问题。正当她觉得自己要开始的时候,问题出现了。一位顾客拿来一件毛衣,让她改一下。
这难倒了她——她接触的编织服装比较多,不仅很少接触到这件毛衣,而且当时师傅也没教。入冬后大家的生意都很忙,她也不好意思打扰老爷子,只好接单改改。
由于她不懂毛衣编织的原理,所以她改的衣服第二天就脱了。顾客把脱下的毛衣穿在身上出丑了,她羞得满脸通红,花了一整天时间重新缝制毛衣。

经过不断的研究和实验,她终于改进了这件毛衣。同时,她还学会了毛衣织补的一切。这件事让她久久难以忘怀,也让她懂得了“破布是最好的老师”。
接下来的几年里,她靠着这种钻研精神,完成了各种高难度衣物的补补工作。我们也有很多常客。
“如果贵州下雨,就应该过冬。”入秋后,天气转凉。大多数市民都穿上了长袖秋装,但缝补的姑娘们大多穿上了厚毛呢大衣或羽绒服。 “我在户外坐了一整天,不穿这么厚的衣服,身体就受不了了。”
气温下降对身体不太友好,但对补补生意来说却是好事——天气越冷,来补大衣、羽绒服的人就越多,能赚到的钱就越多。
天气冷的时候,他们一天能挣100多元,但天气热的时候,他们就不行了。生意惨淡,很多人不得不暂时转行,寻找其他零工来贴补家庭收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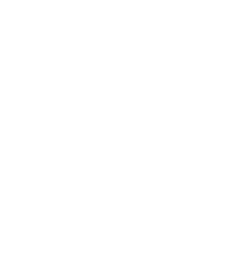
努力工作谋生——为了家人
补补的工具很简单,放在一个小盒子里,就是一些小剪刀、钩针、木担架和大大小小的绣花针。
每件工具都因频繁使用而变得闪亮。这些看似简单的工具却能让一件破损的衣服变得完美如初。事实上,织补是一项艰苦的工作。你大部分时间都坐着不动,这对你的眼睛来说非常困难。 “有时补一件衣服要两三个小时,眼睛累得红肿,流眼泪。”潘文民戴着老花镜一边缝纫一边说道。有些顾客急着需要衣服,我们想中间休息一下。一时半会不行,只能赶紧赶进度。

10多年前,在外打工的潘文民为了陪伴儿子、女儿读书,回到凯里。生意好的时候,她就带着孩子一起去。女儿沉浸在其中,学会了刺绣、补补,有时甚至还修改自己的衣服。目睹母亲的辛苦,乖巧懂事的女儿也努力学习,现已考上大学。她有一个不同的职业计划——成为一名电气工程师。
冬夏交替,这些苗族妇女骑着小马已经十几年甚至半辈子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关心自己的孩子。
田映秀的情况就更加特殊了。她的女儿生来就是聋哑人。为了陪伴女儿到大十字旁边的特殊教育学校读书,她加入了补补女孩的队伍。他早上第一个来送女儿上学;不管下午生意多好,女儿放学后他就关门了。令她欣慰的是,在政府的医疗援助下,她的女儿安装了人工耳蜗,能够像正常孩子一样说话和唱歌。
工作间隙,她会翻出女儿录的视频看,“我有一个好妈妈,我的妈妈是世界上最美丽的人……”看着女儿大方的表情,田映秀觉得无论工作多累,她心里都是甜甜的。

织补工艺在大城市很有价值。几年前,凯里街头,一位广西顾客请田映秀补一件大衣。他每年都会送几次衣服给她缝补。通过与顾客的交谈,他们还了解了其他地方补补的价格——一个小洞20到50元不等,相当于他们辛辛苦苦缝补的一件衣服的价格。因此,一些织补女孩去其他地方追求更高的收入。大家也很羡慕那些出去赚钱的人,但为了孩子和家庭,他们还是留在了凯里。
在工作中,织补姑娘追求每一针的完美和极致,将工匠的思想融入到面料中,销往千家万户。织补姑娘一生中,把自己的时间和精力都奉献给了孩子的培养和家庭的养育。细心呵护,就会得到生命的回报。旧衣服、破洞、密密麻麻的缝线交织在一起,见证着他们对技艺的追求,以及对生活的感恩和热爱。
结尾
版权声明:本文内容由互联网用户自发贡献,该文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本站仅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不拥有所有权,不承担相关法律责任。如发现本站有涉嫌抄袭侵权/违法违规的内容, 请联系本站,一经查实,本站将立刻删除。如若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s://www.fxk666.com/html/tiyuwenda/800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