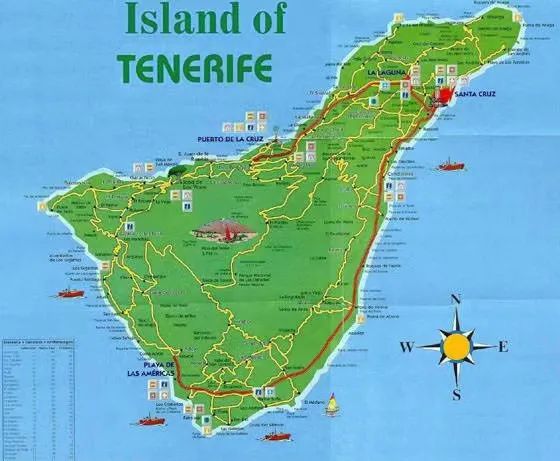时间的媒介化建构
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时间越来越依赖符号媒体来表达自己。这种依靠媒介构建的时间不仅是人们活动的尺度,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时间规划和意义体验。与产业资本对人的精神世界和意义空间的漠视不同,数字资本特意将人的意义空间作为建构和塑造的对象。按照马克思的分析,“人不仅在精神上和意识上使自己二元化,而且还主动地、现实地使自己二元化,从而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地认识自己”。 “二元化”意味着人本质上追求超越意义,意义空间的大小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人的存在和发展方式。作为人类本质力量客观化的产物,数字技术本身也是确认人类存在意义的工具或媒介。

从根本上来说,意义空间并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植根于人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但同时,人的意义空间又超越了现实生活过程的机械性和僵化性,从而构成了人的更高层次。确认个性的超越境界。古希腊哲学家对人类精神生活的孜孜追求,正是为了追寻和确认存在的独特意义。马克思说:“与现代世界相比,古代的观点要高尚得多。根据古代的观点,人们无论处于多么狭隘的民族、宗教或政治规则中,总是表现得像有生产力的人。目的,在于现代世界,生产代表了人类的目的,而财富则代表了生产的目的”,数字技术具有构建超越意义空间的强大功能。它通过将日常活动的时间数字化,以清晰可见的方式创造意义空间,使意义变得可见、可感知,从而使意义变得可见、可感知。主体的个性、创造力等内容被生动地呈现。但不可否认的是,人们在数字空间中度过的日常生活时间往往是由翻新的景观和符号所诱发的。对数字空间中抽象景观和符号的依赖取代了人们对意义世界的个性化体验。这无疑远非真正的人格确认。按照道格拉斯·凯尔纳的理解,这种越轨的根本局限性在于“景观的‘顺从消费’使人们远离了生活的积极参与和创造”。这样,越多的人通过数字网络技术确认自己的个性,就越会在符号和风景的崇拜中迷失自我。这种以“恶无限”为特征的追求,不但不能引领人们的精神世界舒展、安宁。相反,它们正在悄悄地按照数字资本的形象塑造自己,让人们臣服于数字资本的增殖逻辑,精神变得飘忽不定、无所适从。
观众操作时间

数字资本时间规划的中介环节是时间的商品化。时间的商品化是指数字资本利用数字技术将生活领域的时间转化为有偿或无偿的商品形式,从而将所有形式的生活时间卷入资本增殖的漩涡中。应该说,20世纪下半叶消费社会兴起期间,生活时间已经开始了广泛商品化的过程。鲍德里亚所揭示的消费社会正是在批判人们的闲暇时间在生产领域之外被编码的方式。调控新条件。消费社会改变了早期资本主义忽视生命时间、压制个性的野蛮做法,进而将消费所宣扬的个性纳入资本控制的逻辑之中。达拉斯·斯迈思提出的受众商品理论从另一个角度揭示了传播行为在资本增殖中的独特作用。他认为,受众商品是指受众群体的关注时间。这个时候与观众的收视行为紧密结合,可以被媒体打包卖给广告商。这就形成了广告商、电视台和观众三位一体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广告主从电视台、广播电台等传统媒体购买受众的注意力时间,受众为广告主进行免费的受众劳动,即观看。在受众的注意力时间被包装作为商品卖给广告商的前提下,受众的工作时间除了睡眠时间之外都被广告商占据。也就是说,受众正在通过无偿的受众劳动接收广告信息,推动消费从潜在向现实的转变,从而加速资本的循环。
在数字技术的推动下,通过以受众为导向的数字劳动,时间的商品化已达到普遍水平。这意味着数字平台与广大用户的关系不仅仅是为用户提供服务的关系。事实上,观众在消耗自己浏览、观看等时间的过程中,也在向数字平台提供无偿劳动。这种劳动以注意力时间或观看时间的形式提供。数字资本根据平台的使用价值获得数字劳动者的劳动时间,并将这段时间商业化,出售给广告商。就此而言,人们在互联网上消费日常生活时间的过程自然与数字资本的泛滥联系在一起,人们的日常生活时间也因此普遍商品化。人们的消费时间、娱乐时间、审美时间等时间形式都不同程度地被吸纳到网络平台中,成为数字资本增殖的内在环节。因此,数字技术所推动的日常生活时代,蕴藏着人们与这些以受众为中心的时代的疏离和对抗。当人们的日常生活时间没有强大的数字技术介导时,人们的消费、娱乐、审美时间在很大程度上按照主体自身的需要自然展开。在这个过程中,时间只是表达或记录人的活动。这是一种积极、主动的时间表达方式。然而,在数字技术的压力下,这些活动时间实际上是从外部强加给活动主体的,个体只能被动地接受那种充满控制论兴趣的时间。数字平台作为一个具有自我扩展特性的系统,需要不断分化和重组人们的日常生活时间,并使其服从和服务于其背后的增殖逻辑。因此,我们越来越感觉到生命的时间在很大程度上被数字技术绑架了。时间作为生命的坐标和变量,获得了强烈的吸附和膨胀。人们必须按照数字技术提供的方式来计划和计划。度过你的空闲时间。
非线性时间规划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按照资本增殖的逻辑,将劳动时间与人的生命时间分开,从而实现社会生活的时间重构。在工业资本主义早期,生产时间的发展是建立在一定的物理空间基础上的。因此,劳动时间与生活时间、工作时间与生活时间整体上呈线性展开。在这种基于线性时间的时间规划中,资本家试图最大限度地将流逝的时间以物的形式固化,从而形成财富的物化形式。数字资本主义利用数字技术创造出时空融合的新空间,实现了空间的高度融合与深度分化的有机结合,并在此基础上重构了以往的线性时间结构和时间体验。空间高度整合意味着数字网络技术按照数字网络空间的整合逻辑来运作以前相对清晰的生产空间和生活空间、地域和空间关系的界限。同时,高度整合的空间进一步加剧了不同空间类型和空间关系的深度分化。因为任何一种空间生产都是由人类活动驱动的,而人们可以通过数字化活动在各种空间中移动、旅行,空间也在加速分化和裂变。这导致了空间和时间的重建。

非线性时间结构是空间高度集成与深度分化相互作用的产物。其突出特点是把过去、现代和未来的时间全部融入到同一个数字空间系统中。例如,我们使用微信语音消息功能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突破对话所需的相同上下文。例如,人们还可以利用碎片时间来完成不需要立即完成的任务。这些是数字技术创建的非线性时间场景。从这个意义上说,非线性时间实际上已经嵌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与每个个体的生命过程密切相关。非线性的时间结构将引起人们的生活态度和生活感受的本质变化。一方面,它可以让人们更有效地安排自己的生活时间,使生活活动的内容更加符合自身的发展需要;但另一方面,非线性时间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人们对过去和未来的感知,导致人们过于关注当下。就过去而言,过去并不是简单地以记忆或回忆的形式呈现。从这个意义上说,过去不再以现在作为考察的尺度。所以,过去的事情其实并没有过去。这就改写了人们过去的意识,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历史意识;就未来而言,未来不再单纯是基于现在为坐标对未来的设计和想象。所以,未来实际上蕴藏在人们的感性直觉之中。
总而言之,数字资本主义的时间重构不仅将人们带入了新的生活境地,而且赋予了时间资本的属性,呈现出前所未有的辩证张力。如何面对数字资本对时间的重构及其社会历史效应,推动解放政治意义上的时间解放和时间文明建设,是唯物史观必须面对的当代问题。
(作者单位:西北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版权声明:本文内容由互联网用户自发贡献,该文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本站仅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不拥有所有权,不承担相关法律责任。如发现本站有涉嫌抄袭侵权/违法违规的内容, 请联系本站,一经查实,本站将立刻删除。如若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s://www.fxk666.com/html/tiyuwenda/2073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