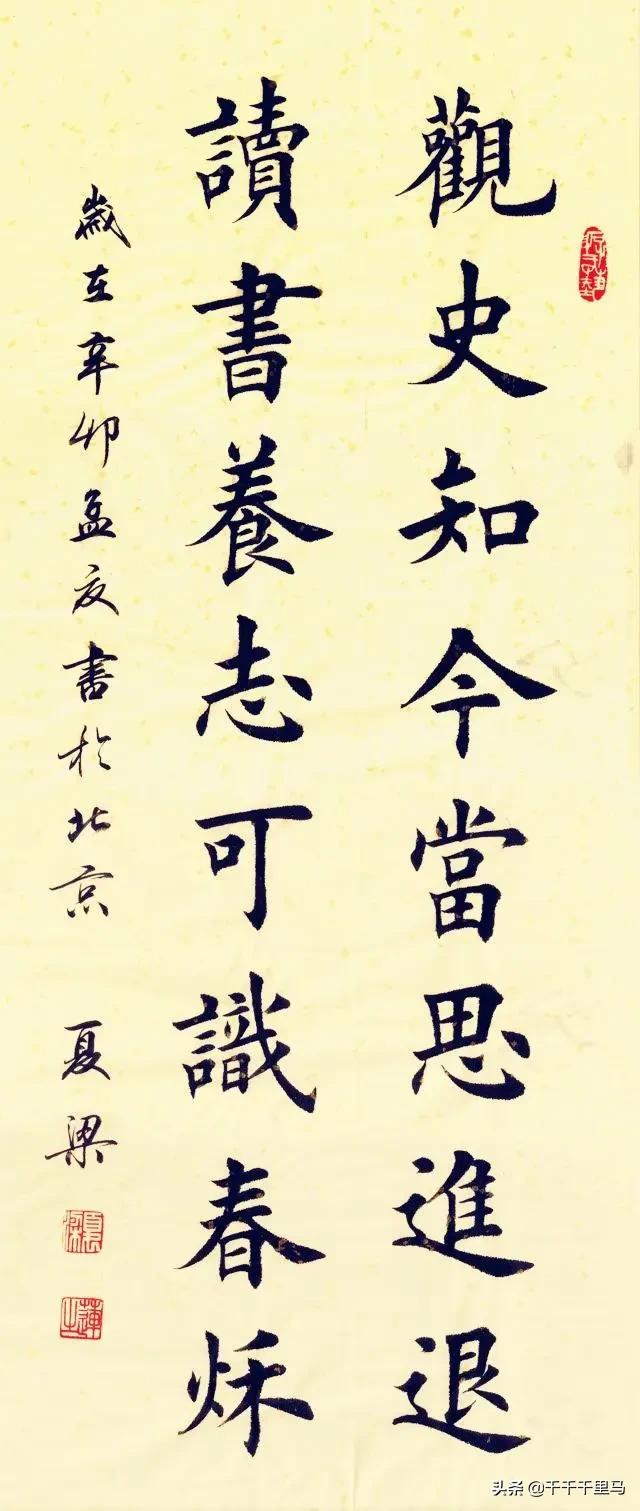——独家专访德国科学院院士郎米歇
中国的预测是基于计算的。 《易经》是延续至今的中国预言的核心。预测是通过对西洋蓍草进行复杂的分离而做出的。西方的预言都是出自先知之口。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 刘耕/上海报道
德国国家科学院院士朗米舍是一位会算命的汉学家。他目前领导的研究机构的标志是一个圆圈里的“明”字。
批八字、抛龙杯、练奇门遁甲,是他学术研究的需要。在西方汉学界,郎米歇以精通多种语言、学术领域广阔而闻名。他的妻子说他“有上进心”,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周振和则说他“爱搞怪”学习。
事实上,郎米勰的汉学之路很大程度上是从他对宋明理学的研究开始的。他是宋代表演学者张载德文版《正猛》的两位译者之一。 2014年3月,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德国期间会见了郎米歇等多位汉学家。郎米歇当时问了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儒家思想在习近平主席心中的地位。
“他的回答很坦诚。他说,按照儒家的观点,从长远来看,正义比正义更重要,但我们不能完全鄙视‘利’,应该给人民更多真正的‘利’,平衡正义。”并受益匪浅。”郎米歇向《瞭望东方周刊》回忆。

“我们现在都说中国文化多元,儒学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如果高估它的重要性,我担心儒学将来会成为中国唯一的思想流派。”郎米勰说,“新儒学不能只注重自身的辉煌历史,不能过度强化儒学在中国传统中的作用而过于接近政治,政府应该平等对待所有学术派别。”
2014年9月,郎米歇在复旦大学进行了四场讲座。第一场讲座《小路有理:中欧预报技术比较研究》吸引了最多的听众。
预测被中国《四库全书》主编纪云称为“小道”,被阿尔伯特大帝(约1200-1280年,德国理论家、主教、科学家)称为“小道”——记者注)在欧洲。这就是“不确定的艺术”。郎米歇表示,他的理想是把预测技术从小路带到“大路”,融入国学。
他说:“我不否认命理学是中国传统知识中的‘小道’,但它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却很常见。严复的宇宙观完全是从西方学来的,但他每周都会做占卜,询问有关你的健康、财富等;吴宓是一个很开明的知识分子,但他也在女儿结婚前读《日书》来选择日期。
计划与预言
《瞭望东方周刊》:西方和中国的文明传统都对命理学预测未来有着浓厚的兴趣。中西方预测有何异同?
郎米歇:预测是人类的共同利益,但东西方对于命运和自由的态度不同,发展路径和优先顺序也不同。

中国的预测是基于计算的。 《易经》是延续至今的中国预言的核心。预测是通过欧蓍草的复杂分离来预测的。西方的预言都是从先知的口中得知的。古希腊提到阿波罗神(德尔斐预言的大师)。 )被视为皮提亚预言的灵感来源,自公元前八世纪以来一直盛行,当时达官贵人会长途跋涉数千英里前往德尔菲神庙询问特定问题或事件。新约中的预言也是启示,耶稣自己就是先知。
当然,这两种预测方法在东方和西方都存在。中国的先知具体体现在萨满教、巫术、富士科技等方面。尽管有上层学者参与这些活动,但中国的预言仍然是一种边缘现象。西方也有基于计算的预测科学,例如占卜,但不太发达。在古希腊和古罗马,占卜活动主要流行于普通民众,先知是西方的高级文化。
还有彩票。从古希腊到中世纪末期,彩票在西方非常普遍。这是对普通人的预测。它的技术含量低,不是高水平的文化。中国易经的方法基本上可以看作是抽签,但易经是文化的精髓。
从预测技术来看,中国比西方更发达。除了占星学之外,没有什么禁区——占星学被朝廷垄断,主要局限于“天垂看凶”。它具有政治敏感性,不能由个人实施。其他预测技术多种多样,大部分源自《周易》。在西方,占星学更为发达。
中国和西方的占星学都是一门天地间的伟大科学,建立在天人互动的基础上,建立在对天人的认识基础上,从各自的文化语境出发。西方占星学催生了“占星医学”和“占星气象学”,而中国则利用阴阳和五行来构建占星世界。西方的出生占星学可以与中国的星座算命相比较。 13世纪的博纳迪相信《天文经》认为,占星术可以解答何时破土吉祥顺利等问题,与中国的“择吉术”有可比性。
中国预言中的“占卜”人与西方有很多相似之处;而“占卜”的地方,即看风水,则在西方是没有的。
另一个根本区别是宇宙学。根据基督教的说法,宇宙之上还有另一个层面,那就是上帝。神的态度和行动是不可预测的。传统中国没有上帝的概念。有人提出,中国人讲天人合一,就是说我们按照我们所理解的宇宙规律做事。宇宙有规律,人类也是宇宙的一部分。如果我们能够推理出宇宙的规律,也就能够推理出个人的命运。这种观点有一定道理,但过于简单化。
迷信与命运
《瞭望东方周刊》:命理学和预测被一些人视为科学,而另一些人则批评它们是迷信。这是科学还是迷信?
兰格里奇:阿尔伯特大帝试图将占星学融入科学。他把科学分为两类:一类是基于对原因的调查;另一类是基于对原因的调查。另一个基于对预兆的猜测。占星学被认为是“推测”或概率的科学。
然而,在基督教占主导地位的西方,试图探索上帝的秘密是一种罪过。因此,天主教经常禁止占星术、骰子和其他预兆。随着基督教的流行,预测在西方不再占据主导地位。但仅仅是残余现象。欧洲启蒙运动利用科学来消除预感。
中国历朝历代在不同时期将不同的占卜术定为秘术,但占卜作为一个整体从未被宣布为“迷信”而被禁止。它并非与中国文化相反,而是被许多家庭所包容和吸收。意识和民族礼仪。
中文的“迷信”是一个外来词。西方的“迷信”概念经历了基督教和启蒙运动,其意义已被掏空。它已经成为一种批评性的话语并且是消极的。
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洲启蒙思想流入中国,直接导致了1928年和1930年中国的“反迷信”立法运动。在此期间,不仅许多寺庙被迫关闭他们的门,但许多算命师被禁止执业。然而,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仍然拥有20世纪最著名的三位命理学大师:徐乐吾、袁术山、魏千里。

袁术山所著《名谱》,为孔子等64位名人写传记,解释了孔子三岁丧父的原因。尽管当时的国民党当局大力提倡启蒙、启蒙,但占卜书籍仍然很受欢迎。
1949年以后,“迷信”的概念被更广泛地使用。 “文化大革命”期间,占卜等“传统封建”生活方式被禁止;改革开放后,预兆书籍成为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可以在书店买到。但算命作为一种实践仍然处于灰色地带。
《瞭望东方周刊》:中国人相信一个人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和运气。
郎米歇:命理学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对自由命运的理解。预测可以无限重复,并且是自由表达。人们常说中国古代缺乏自由观念或者说自由观念很弱。然而,在相信命运预测的文明中,理论上可以利用从专注中获得的知识来调解命运并获得自由。 。
许多与命运谈判的形式都是从中国古代流传下来的。从魔法到道德和修身,通过祭祀来取悦祖先或者按照“日术”的指导行事,以及在佛教世界中,可以改善业力,减少甚至完全抵消负面后果——佛经中的“追善恶业”圣经就讲到了这个问题。马克斯·韦伯称中国传统为“根本的存在主义乐观主义”,因为自由可以通过每天与命运的谈判来实现。
“大数据”与预测
《瞭望东方周刊》:现在“大数据”很流行,人们甚至用它来预测消费者购买行为、世界杯足球锦标赛等,您怎么看?
郎米歇:大数据预测和概率密切相关。欧洲在18世纪到19世纪的过渡时期出现了多种形式的所谓“科学预测”,主要采用概率计算。
概率计算和赌博密切相关。预测数据的处理首先由数学家高斯用他的正态分布来表达,后来演变为钟形曲线。自1844年以来,钟形曲线被广泛应用于概率计算,我们或许能够对钟形曲线峰值处的事件做出“科学预测”。然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预测钟声边缘的事件是不可能的。
柏林墙的倒塌、雷曼银行破产引发的经济危机,以及许多与我们息息相关的政治经济事件,都无法用这种概率计算来预测。我们每天都会经历预测,尤其是经济领域的预测,一直在被修改。
很明显,预测的价值在不断被侵蚀,尤其是涉及个人的预测,比如医学,预测的价值很低。三年前,我患了腰椎间盘突出症。我看了五位医生,得到了五种不同的答案。
现在政治学和经济学都有预测,而且都声称有科学方法。政治学家和经济学家成为中国商代的算命先生。每个人都认识他们,甚至崇拜他们。我们德国有五位所谓的“经济之神”。老百姓都相信他们。然而,一周后,他们往往会改变态度。
《瞭望东方周刊》:那为什么还需要先发制人的艺术呢?
郎米歇:人类无法忍受缺乏意义和绝对的随机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歌德在自传《诗与真理》中称自己为“迷信”。自传的开篇就是他出生的时间。他说:“迷信是一个充满独立、进步、自然的世界。软弱、狭隘、犹豫、困于自我的人的特点是什么都不相信。”正因为如此,歌德非常重视预言。
人类面对未来迫切需要安全感。我们经历的事件,包括意外,都应该有意义,否则,恐怕会很无聊、很悲观。然而,每种文化和每个人对于如何构建和解构这些意义都会有不同的看法。
版权声明:本文内容由互联网用户自发贡献,该文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本站仅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不拥有所有权,不承担相关法律责任。如发现本站有涉嫌抄袭侵权/违法违规的内容, 请联系本站,一经查实,本站将立刻删除。如若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s://www.fxk666.com/html/tiyuwenda/14088.html